〔凌李〕石头记(一发完)
warning:打乱的原剧时间线。以及,是并没有什么机会吃吃喝喝的凌李。
丨。
2013年11月10日晚上十点三十二分,李熏然在警务值班室刚冲开了一盒泡面,没来得及吸溜两口热乎的,值班室里就走进来一个高大的男人。
“警官你好,我要报案。”
泡面碗沿的那层塑料纸只划拉开了半个口子,熏然把翘起来的那层纸又拿手机压住了。
来报案的这个人,从进门起情绪就很镇静稳定,身上还是衣冠齐楚的,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头装了好几罐啤酒,但人又不像是喝醉了。
看着应该也没有遭受什么身体伤害,估计不是什么恶性事件。李熏然一番观察,在心里做了个初步的判断,暗松一口气。示意报案人在他对面坐下,点开电脑桌面上的报案记录系统,开始例行的询问和记录。
“能简单说说什么情况吗?”
“十点十分左右,刚从便利店里买完东西出来,公文包就被飞车党抢了。”报案人无奈地扬了扬手里的塑料袋,在安静的值班室里发出突兀的窸窸窣窣声,“我所有的身份证件和工作资料都在里面,应该还有两张银行卡和一万块现金,哦对,还有我的车、我家和我单位的好几串钥匙。”
“嗯,好的。”李熏然简单地回应着,一面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您有受到什么伤害吗?”
“没有。他们速度很快,我也没硬揪着不放。”
“那就好。”
李熏然还在打着字,真正值班的小周带着另外两个人从外头回来了,前脚刚踏进门就急吼吼地说:“李队,楼上证鉴科说分析结果出来了——啊,有人报案?”
李熏然敲下最后一个标点,腾地一下赶紧从位子上站起来,揣了手机就要往外走。又绕回来抱歉地对报案人说:“不好意思,您的案子他会继续帮您记录的,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抓住嫌犯。”说完一面冲小周示意他跟进,一面脚下生风地走了。
小周坐回李熏然的位子,大致扫了眼案情记录,已经录得差不多了。
“您的姓名?”
“凌远。凌厉的凌,遥远的远。”
一旁的打印机咔啦啦地吐出一张纸,小周抽过来又再看了眼,然后递给了报案人,说:“您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请在报案人那一栏签个字。”
凌远接过记录单也扫了眼,凌厉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抬头把纸递回去的时候,看到了桌面上刚才那个警官压根没吃的泡面,划拉开的半张塑料纸翘在空中,热气氤氲成水珠浮在纸面上,不一会儿又沿着表面坠落下去。
。丨
三个月后,凌远再见到李熏然,是在杏林分院通过消防验收后他自己攒的一个饭局上。
凌远自己不是那种有歪心思的人,饭局上请的,也都是老院长还在任时就跟附院一直有交集的公安和消防系统的老领导们。老院长的人情交往能延续到了凌远这儿,一来是大家都清清白白地务实,二来则是抛去公务公事,这些平日里总得虚虚实实的人,见了凌远这样的后生,多少也愿意更亲近一些。因此,说是饭局,倒也不如说是老领导们和凌远这样的忘年交,借着由头的小聚罢了。
于是李局长一听消防局的陈局准备携夫人出席,还带了自己珍藏的一瓶好酒,没做他想地就叫上了熏然。
李熏然倒是不常跟他爸一起去这样的饭局。他爸喝多了话虽不多,但容易逮着个人就夸自己,平常那些轻易说不出口的得意和自豪,在酒酣耳热之后轻轻快快地就倾吐而出。李熏然面薄,知道他爸的脾性,自然也是能躲就躲,实在躲不过的时候,就只能尽量不让他爸喝多。
今天这顿饭,除了做东的凌院长,其他人都是李熏然从小就叫着叔叔阿姨的人。恰巧昨天刚结了一桩入室杀人案,熏然也想好好放松一下,因此跟着他爸来凑局,倒也自在地一直埋头苦吃,一面在记忆里搜索,隔着一桌好菜,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凌院长,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桌上的话题绕了一圈,终于落到了凌院长的私生活上。
陈夫人一直很关怀凌远,凌远是能感受到的,自然也明白这几位长辈不是八卦的人,倒也坦承相对了。
“我和念初吧,到底还是离婚了。”凌远一时不知该把眼神落在何处,越过桌上的杯盘狼藉,倒是见到了一个正低头专心对付食物的头顶,微微蜷曲的头发温柔地互相纠缠着,听见了八卦似乎也没有什么探究的心思。
“念初和你都是好孩子,你们呀,就是太要强了些……”
陈夫人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话,刚刚还在埋头苦吃的青年,看到桌上的手机震了几下,便抬起头来跟大伙儿致个歉,伸出舌头舔舔嘴唇,起身就去外头接电话。
凌远突然记起来了,眼前这个分外眼熟的青年,是他跟念初签字的那晚,去警局报案时,那个泡面都没来得及吃两口的警官。
叫什么来着?
哦,李熏然。
丨。
李熏然这晚接到出警通知的时候,在路上看了已经成为网上热点新闻的视频。
一个新生儿的父亲,因为护士给小儿扎针时没能一次成功,一怒之下操起墙根的灭火器就往小护士的头上砸去。那样重的一个灭火器砸得变了形,护士被送去抢救,墙上、地上汪着一片片夸张的血迹。那发了狂的男子竟然又挟持了一名儿科大夫,拿着不晓得哪里来的小刀抵着大夫的颈动脉,叫嚣着不给他家小孩好好治就要大夫以命抵命。身上的白袍被鲜血溅了一身的凌院长,在视频里筋疲力尽地跟发狂的人沟通,场面却在画面突然跑进一个小护士时失了控。慌慌张张的小护士带着哭腔喊:“院长!院长!……小林她……她没救过来……”于是失去了耐性的凌远,一阵风似的扑倒了家属顺势把大夫推开,又一拳挥上了那人的下巴。视频的画面抖得不成像,围观群众一声声的惊呼。
被人拉开的凌远在画面里冲地上的人咆哮:“你他妈还配当个父亲!”被骂的那个,躺在别人的血泊里,痛得呻吟。
第一医院的院长公然殴打病人家属,被打的人揪了七八个亲属在院门外拉了布条闹着。而不知哪位有正义感的路人,在门口的台阶上献了两支白花后,竟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看了视频后带着鲜花或蜡烛过来了。
李熏然他们在人群中拉上警戒线,心想,守护伊甸园的长天使的确不好当啊,得跟撒旦争论,还要与魔鬼争战。也不知道那个无辜的孩子怎么样了。
这乱糟糟的人间。
一边是家属在声嘶力竭地嚎啕,一边是越来越多自发来致哀的人群,错杂的脚步声渐渐临近,恢复了气度的凌院长走在最前头,领着身后的一群白袍绿衣,走下了台阶。他们或点上蜡烛,或献上白花,背对着身后的人群,面朝着医院的大门,鞠躬,默哀。
凌远走向胡搅蛮缠的人,居高临下:“孩子已经退烧了,你们若还有心想为孩子好,就先找人带回家照顾。孩子他爸如果需要验伤,尽管验;想要掰扯孩子的治疗问题,尽管找第三方调查机构来介入;我们医院之前已损失了很好的产科大夫,再面对这样的事,我们绝对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力,你们爱在这儿坐多久就坐多久吧,我们去法庭上沟通。”
凌远欲拂袖而去,家属一听却不依了,七八个人围上去就要揪住凌远不放。李熏然几个眼疾手快地冲上前去挡在中间,黑衣与白衣汇合,划成两条分明的线。
家属还在不依不挠地推推搡搡,李熏然一个擒拿制住了带头的人,几个警员也在旁一一苦心相劝。
凌远得以脱身而出,隔着混乱的人员冲熏然感激地点点头:又补充道“我们医院愿意配合警察做任何调查。”
闹事的人手脚还被压制着,李熏然擒着人半跪在地上,仰头向凌远示意,彼此的疲累和坚持都写在了脸上。凌远怎么带着人出来的,就怎么带着人回到各自的岗位上。
李熏然看着他们被脚风带起的医师袍低低地翻飞着,仿佛看到了一座座在风浪中安然不动的白色巨塔。
。丨
凌远后来再回想,跟李熏然相熟起来的那段时间,正好是他最焦头烂额的时候。
在那间他们偶尔能相遇的健身房的桑拿间,李熏然一边扒拉着他的卷毛,一边亮晶晶地睁着一双圆圆的眼睛,安静地听他向他吐吐苦水。
凌远自认不是一个喜欢主动诉苦的人,更不是一个嘴碎的人。然而他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每一次在热气腾腾的桑拿间里,只要李熏然的眼睛一望向他,问他一句“老凌最近医院还太平么”,他就会忍不住向李熏然讲一讲那些跟鲜血与生死相关的事——告诉他普外科轻症组的成立和推行有多难,告诉他生殖中心的龌龊之事有多难堪,告诉他如何不忍心看到自己的爱徒在情爱的纠葛里苦苦挣扎,甚至还把自己最狗血的人生血淋淋地摊开了……
凌远自知是个懦弱疯狂又自私凉薄的人。他难以自控地想要把最无能、最丑陋却又最真实的那部分自己剖开,再作为呈堂证供一般,毫无保留地呈阅给李熏然看。
可能,是因为面对着一位人民警察,凌远下意识地想要坦白从宽。
或许,是因为关怀他的人,每天面对的也是鲜血与生死,凌远相信,毋须过多的解释,那双黑白分明的眼自然能一眼看透他。
大概,当身边所有的人都在以各式各样的标准要求他、质疑他、指责他的时候,竟然在一间温暖的桑拿房里,还有一个人愿意静静地聆听他、安慰他——几乎是本能,凌远没有办法不去靠近他。
李熏然当然也会跟他讲一讲自己最隐秘的那部分纠结,与他抱怨一下蹲守和逮捕的艰难,与他感叹一下罪恶的黑暗与嚣张,与他倾吐自己暗恋了多年的姑娘最终喜欢上了另一个他……
凌远觉得,他们俩,一个是自己拿起手术刀剖开了溃脓的血肉;另一个则是拉着挥刀的人,一起躲在那间小小的桑拿房里,躲在一个只有他们俩才知道的幽冥之地,温柔地舔舐着彼此的伤。
他们啊,都不是一时兴起而奔波在碌碌红尘里的人。这一生,各自选择了执一黑与一白,便都想毫不犹豫地守住这两道分分明明的人间防线。
即便跌跌撞撞,也要不离不弃,莫失莫忘。
丨。
很久以后,李熏然才知道,自己在凌远的记忆里,留下了许多个揣起手机就风风火火推开门去的身影。
那天他在桑拿房里接到薄靳言的电话时,他们俩谁也没有想到,再见凌远的时候,李熏然会是那样破碎的自己。
他用悬丝般的最后意志,朝自己身上开了两枪,暖烘烘的热血喷溅在冰凉的墙面上,曾经那样强大的意志,也随着破碎的玻璃轰然坍塌。李熏然想——结束了,一切都可以结束了,那个名叫谢晗的魔鬼企图把他雕刻成一件作品,那他就只能把自己掰碎了,再撒在那条守护线上。
然而,他从痛苦的梦魇中挣扎着醒了过来。
浑身的感官都充斥着恶心,李熏然以为自己已经毫无求生意志,但他还是被人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
委屈。疲累。不甘。麻木。恐惧。消极。
病床前涌过来一张张哭着笑着红着眼的脸,影影幢幢地飘叠在眼前。
“然然……然然……”
他们亲昵地呼唤着他,可是李熏然觉得,那些声音是那样遥远,虚虚实实地撞进他的耳膜,鼓动在他的听觉系统里。他竭尽所能地撕扯出一个又一个笑容,以致消耗了他所有的耐心和力气。
李熏然知道凌远是在后半夜才进屋的。
他闻到空气里甜腻的花香淡去,知道是凌远把夸张的花篮撤走,又带回一身清冽的消毒水的气息。他感觉到凌远坐在他身旁,从口袋里掏出一瓶药倒出药丸就干吞了下去,他猜那大概是凌远一直随身带着的6542。他想睁开眼睛看他一眼,但莫须有的梦正魇着他。
李熏然不知道凌远在他身旁坐了多久,直到一声轻柔却突兀的手机铃声响起来。他的身体几乎和凌远的身体同时反应,凌远正欲起身离开,李熏然却因那声铃音浑身痉挛起来。凌远早就掐掉了电话,可脑子里的旋律已经被触发的李熏然,不由自主地撕扯着浑身上下的各种管子,自己被自己的碎片碾压着……
凌远按响床头的呼叫铃,值班的护士急匆匆地赶到,看到自家院长跪在病床上,手脚并用地箍住了床上的病人,以防他伤害自己。
一针镇定被推送进静脉,李熏然逐渐丧失了力气。
凌远干脆也侧身在病床上躺了下来,手臂还搂着瘦得只剩一把铮铮铁骨的人,冰凉的脚板贴上一样冰凉的脚面。凌远的胃还在抽搐着,胸腔里的空气似乎被一点点地抽走了。他忍不住抱紧了怀里的人,哽咽着跟他一遍遍地道歉:
“李熏然,对不起……”
李熏然很怕凌远也唤他然然。
幸好他没有。
那一晚,李熏然偎着一个冰凉的怀抱,终于跌入黑甜的一觉好眠。
。丨
凌远一直都很坦然地承认,病人与病人是不同的。
他没有办法掩藏自己对冯渺母子的私心。因此,当老源告诉他有合适的肝源可以使用的时候,凌远完全无法拒绝。
他深深地厌恶这样的自己。便只能装模作样地逃到李熏然那里去。
熏然的身体在一点点地恢复,精神不错,却还是很脆弱。要把破碎的自己再一点点揉回去,没那么简单。因此,凌远养成了新的习惯,李熏然的病房俨然成为曾经的那间桑拿房。
冯渺母子的情况,凌远一直断断续续地跟李熏然聊过。凌远其实并不需要多做解释,却还是在李熏然的病床前坐立难安地支吾着。
直到李熏然打着点滴的手抓住了自己的手,凌远蓦地感觉心定了。
李熏然跟他说:“是非黑白必须分明的,是我的工作,不是你的。做医生,从来都没办法只看对错。”
于是,凌远揣着一颗稳稳当当的心,穿过手术室的三重门,坦坦荡荡地站在无影灯下,重重身份只留下了“肝胆第一刀”。
凌远擎着左右两只手,各看一眼站在他左右的李睿和韦天舒,确认了各项指数,然后接过第一把冰凉的手术刀,划开了第一道见血的刀口。
凌远冷着一颗心,又重新穿过手术室的三重门,门外过于喧闹的人声一层一层地裹挟着他,“肝胆第一刀”的凌远,又一步一步地变回第一医院满是争议的凌院长。
直到他推开最后一扇门,看到在门外边,李熏然在缓慢而艰难地踱步。
李熏然趿拉着拖鞋,自己举着一根挂着吊瓶的铁杆子,身上的病号服像两片纸一前一后地贴着身子。迎上李熏然探寻的目光,凌远突然觉得委屈非常。
他极度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面部肌肉,扶着李熏然在人来人往的医院走廊里坐下来,在嘈杂的人声里,缓慢而艰难地向李熏然解释,自己刚刚和他最得力的两个医生,如何完成了一台劈离式取肝手术,如何在开腹后惊讶而绝望地看到病人严重粘连的组织,如何竭尽全力地做了注定失败的吻合……
凌远剜着自己的血肉向李熏然做陈述,麻木中感觉到李熏然张开了怀抱搂住他,冰凉的双手捧住他的头颅,温柔地安抚着他。
李熏然一遍又一遍地说:“没关系呀,没关系……”
于是,凌远无法拒绝地把他那沉重的头颅埋在李熏然单薄的肩颈处,滚烫的泪水坠落到对方的肩窝里。
随着泪水一起破碎坠落的,还有自己那颗心上的囚牢。
。丨。
他们理所当然地生活在了一起后,那是凌远唯一一次陪李熏然训练。
从医院领回来的报告,看过一次就被凌远收起来了。凌远和李熏然都知道,数据只是参考,报告也只是报告。
数据有可能会骗人,唯有自己的心,不会自欺欺人。
体能、格斗、擒拿,李熏然都达标了,但他似乎迟迟没做好射击的考核准备。李熏然在等。凌远便陪他一起等。
这一生,他们早就注定了要握紧白色的手术刀与黑色的手枪——即便跌跌撞撞,也要不离不弃,莫失莫忘。
射击馆里明晃晃的灯光刺得人的眼睛发干。即便戴上了隔音耳罩,枪声仍然可以恍惚在耳畔。
射程尽头的人型靶子,一圈又一圈的白线像一个引人深陷的漩涡。李熏然举枪的手是平稳的,手心却湿漉漉地冒着汗。额上的卷毛汗湿了,贴合成纠结的一缕。
凌远揪着一颗心立在一旁。他无能为力地站立着,克制住要替自己的爱人扣住那个小勾勾的想法。
这残忍而操蛋的人间呐!
然后,凌远终于听到六声枪响。
“想知道我最后怎么开的枪吗?”
骄傲又重回李熏然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里,他潇洒地卸下枪膛,归还手枪,摘掉两人的耳罩,接过凌远递过来的水,也不先喝一口就直接往头上淋。
“我想象着,困在人型靶子的漩涡里的人,是你。”
-f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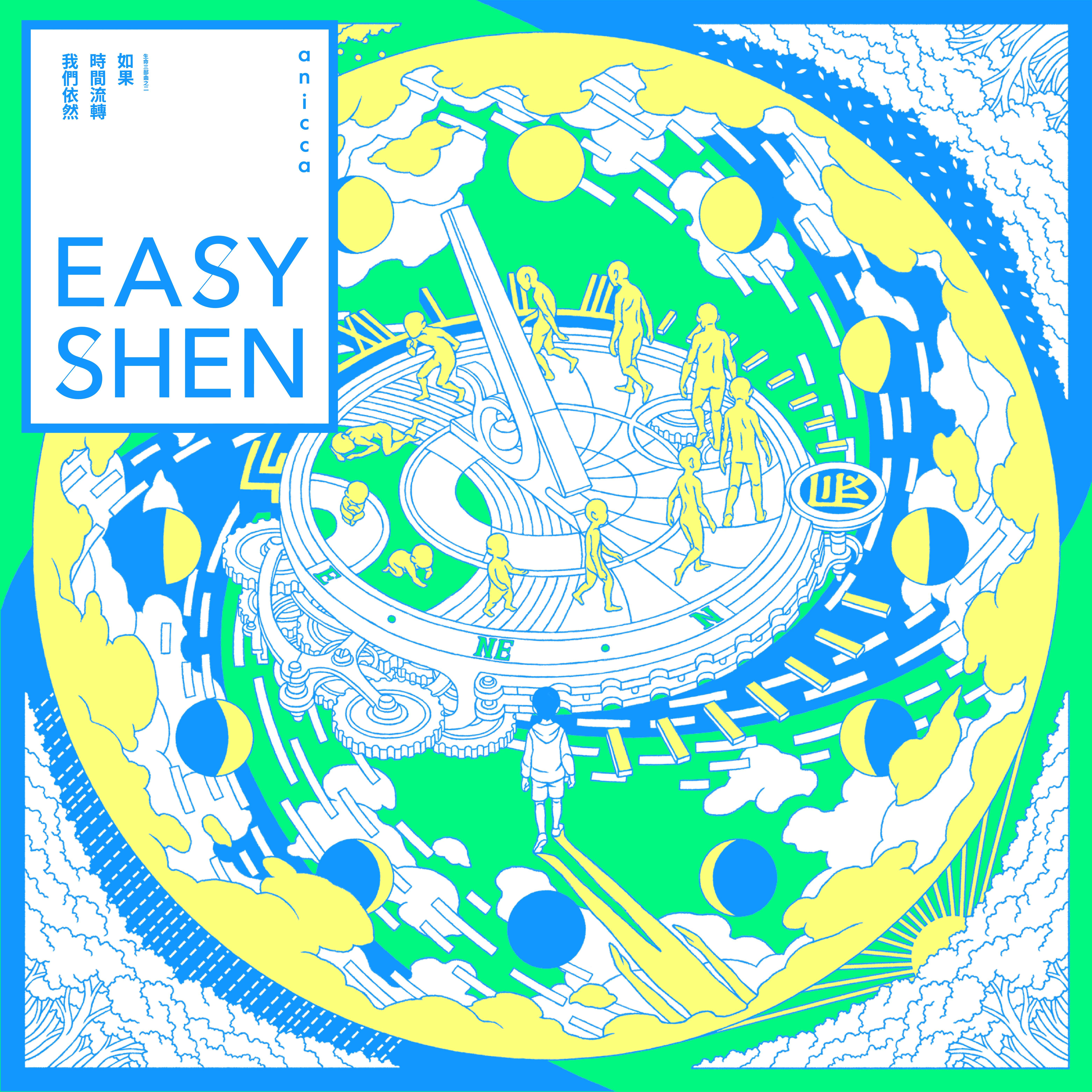

评论(69)